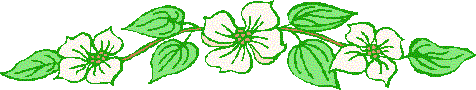|
|
|
祖母走了。三个月前,一百岁高龄的她竟奇迹般地战胜了大量内出血和近四十度的酷暑,却在一礼拜前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,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她生活整整一个世纪的凡世间。祖母走得很快,快到没有留下一句话。祖母的一生虽然物质生活条件很差,但却很完美,她不会有什么未了的心愿,该说的她平时也都说了,能做的她也都做了,任何遗言也许都是多余的。 祖母一生坎坷,前大半辈子多是在战乱和饥饿中度过,最后的日子则备受病痛的折磨。祖母是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村妇人,裹了一双小脚,不足三寸,人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,只呼她八婶或婶婆,说来惭愧,我也是从她的讣告中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。祖母自己没有生育,却有诸多儿女、孙辈、曾孙和玄孙送终。她和祖父先后收养了从印尼回国避乱的伯父,从省城逃到乡下躲避日本鬼子的父亲,以及出生在邻村的姑姑,一家五口各不同姓,祖父祖母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抚养成人。可怜的祖父是在大跃进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活活饿死,祖母她却顽强地活着。 祖母一生淡如清水,身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,她一生大多的时间都花在念经和祷告。对我来说,祖母就象一本充满爱的书,时时在教诲着我。她总是热心为善、乐于助人,从不与左邻右舍有过不快,也极少生过气、骂过人,祖母她多是逆来顺受,就是有谁跟她过不去或得罪于她,也从不放在心上。在我的记忆中,她唯一的一次生气是在我孩提时候,当时我与堂兄打得不可开交。我的记忆中的祖母总是在我生病的时候默默地陪着我,坐在床前为我祷告;在我儿时挨揍的时候总是用自己的身体护着我,让我免受些皮肉之苦;当儿孙们漂泊在异国他乡,她总是日日夜夜在为我们祈祷。我们虽人在天涯,却都可以感受到有一个慈祥的祖母天天在祝福着我们,时时在牵挂着我们,她是我们心中的根。 祖母最后的十多年是在病痛中度过,每次回去看到躺在床上被病魔折腾不成样子的她,我心如刀绞,叹老天不公、长寿非福。祖母是在默默地代儿孙受过,或为了给子孙有个报恩的机会,她自己却要忍受莫大的痛苦。祖母从不会说什么大的道理,但她却在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,她使我懂得这人世间的善与爱,懂得人不能没有根,不可以忘了本,要时存感恩之心。授不图报受知恩,得饶人处且饶人。 祖母出殡时,内亲外戚、左邻右舍、还有本村和附近村庄的热心教友都来为她送上最后一程,队伍长达数里。当我最后目送祖母火化的时候,我竟丝毫没有觉得她已经离开了我们,我知道她在天之灵还会时时刻刻在庇佑着她的子孙。在我默默地为她祷告送行的时候,我恍然间觉得死亡并不可怕,等到我走的那一天,我知道我有一个慈祥的祖母在天国里等着我。 祖母,您安息吧!我们会常常为您祈祷。愿仁慈的天主父、天主子、天主圣神及童贞圣母玛丽娅与您同在。 陈本美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于新加坡 祖母的生前照片 - 1985 1987 1989 1991 2001 2002 2003 2004 亲朋好友
|